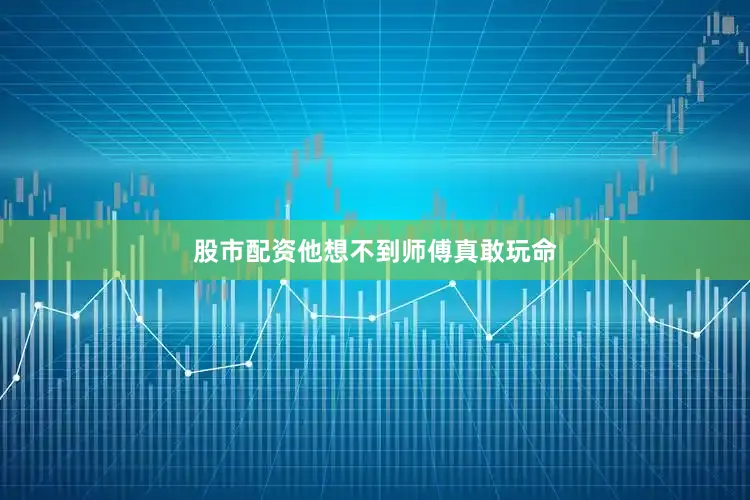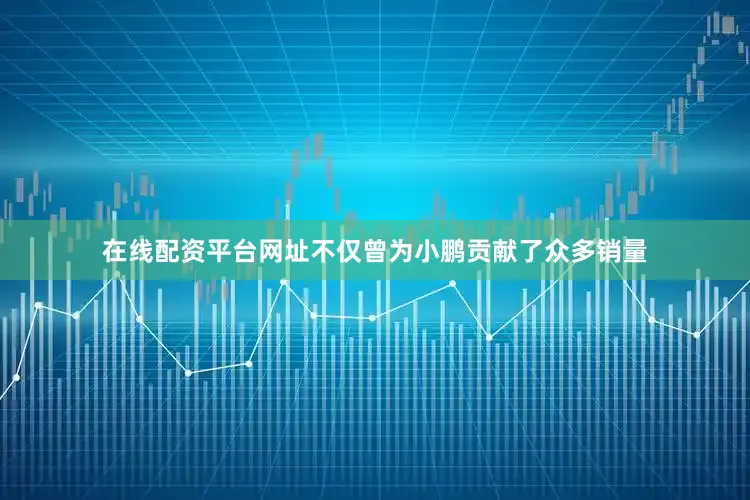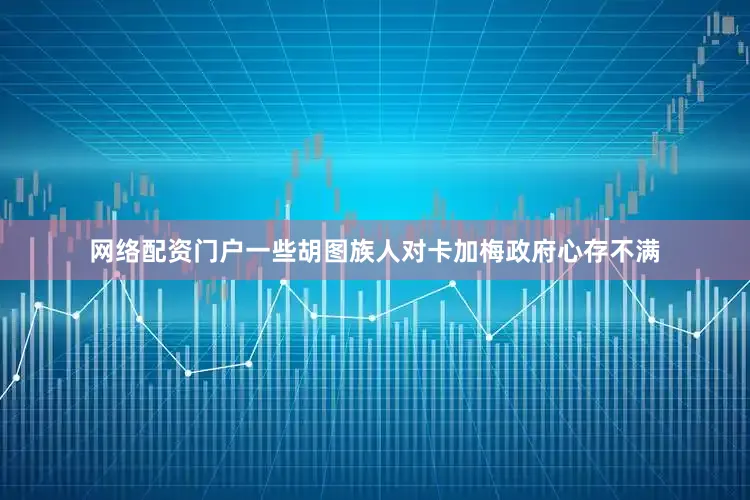哎呀,说起这明朝的藩王,可真是个有意思的话题。
咱们平时总听人家说,明朝的皇帝为了巩固自家的江山,把自己的儿子孙子们都分封到全国各地去当藩王,还立了个规矩,叫“一地一藩”,意思就是说,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藩王,不能扎堆。
这听着挺合理,也挺符合咱们老百姓“一山不容二虎”的朴素道理。
可是,您要是仔细研究研究就会发现,这明朝的藩王分封啊,其实挺多地方都出现过一个地方好几个藩王轮流住的情况,甚至有些王府,换了好几茬主人。
这事儿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奇怪?
明明说好“一地一藩”,咋就成了“王府大联欢”了呢?

今儿个,咱们就来聊聊这背后的门道。
您可能要问了,这明朝的皇帝是不是脑子秀逗了,还是藩王们太好说话,不挑地儿?
其实啊,这背后可不是简简单单的“秀逗”或者“不挑食”能解释的。
这里头,藏着明朝统治者在管理国家、特别是管理宗室方面的一些无奈和妥协。
首先,咱们得说说这最直接的原因,那就是“钱”!
没错,就是钱。
明朝到了中后期,国家财政那叫一个紧张,用咱们老百姓的话说,就是“囊中羞涩”。
您想啊,一个亲王要就藩,那排场可不是一般的大。
得盖王府吧?
王府得修得跟小皇宫似的吧?
这盖房子的钱,可不是小数目。
再加上王爷们日常的开销,那更是一个无底洞。
举个例子您就明白了。
在江西有个地方叫建昌府,那里原来住着一位荆王,叫朱瞻堈。
后来,这位荆王不知道啥原因,迁到别的地方去了。
这下好了,王府空出来了,而且一空就是三十多年!
你想想看,三十年啊,这房子都快成老古董了。
按理说,如果再有新藩王要就藩,是不是得重新盖个新的王府啊?
可明朝政府一看,不行啊,没那么多钱盖新的了!
于是,他们就想了个办法,直接把这个空了三十多年的老王府,赐给了新封的益王朱祐槟。
您瞧瞧,这不就省下一大笔盖房子的钱了吗?
再比如说,河南有个地方叫卫辉府,原来住着汝王朱祐梈。
后来这位汝王犯了事儿,被皇帝给贬了,王府也就空出来了。
明朝政府一看,这地方不错啊,地段好!
于是,就把这汝王府稍微扩建了一下,然后直接给了新封的潞王朱翊镠。
据史料记载,这么一搞,光是盖房子的钱就省了将近三十万两银子!
三十万两啊,这在明朝那可是一笔巨款了,足以买下好几座大宅子了。
所以说,这“循环利用”王府,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财政压力太大,能省一点是一点,谁让国家没钱呢!
这就像咱们老百姓过日子,手头紧的时候,能用旧的就绝不买新的,能省则省,是一个道理。
除了钱的问题,还有个重要的原因,那就是“战略地位”。
有些地方,地理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,用咱们现在的话说,就是“兵家必争之地”,或者“交通枢纽”。
这些地方,皇帝肯定要派自己最信任的亲王去镇守,以保证大明江山的稳定。
就拿湖广的长沙府来说吧,这地方在明朝那可是个“香饽饽”。
它地处要冲,用古话说就是“控雍引扬,襟带江汉”,不仅是平定西南少数民族叛乱的重要据点,还是保障南北漕运畅通的关键节点。
这么重要的地方,皇帝能不重视吗?

所以,长沙府在明朝就先后有四位藩王在那里就藩,分别是潭王、谷王、襄王和吉王。
您看,这王爷们轮番上阵,是不是有点像咱们现在热门小区的房子,一有人搬走,立马就有人排队等着住进去?
还有河南的洛阳府,这地方可是中原地区的粮仓!
伊王被废了之后,福王朱常洵就直接搬进了伊王府的旧址,还大大地扩建了一番。
为啥?
因为洛阳是“控扼中原粮仓”的关键所在啊!
皇帝当然希望自己的亲儿子去镇守这么重要的地方了。
所以说,这些战略要地,就是皇帝眼里的“定海神针”,必须得有自己的亲王坐镇,才能安心。
咱们再来看看一些具体的例子,您就会发现这“王府大联欢”的场面有多频繁了。
就说这湖广长沙府吧,前面提到了,这地方简直就是明朝王府“循环利用”的典范!
一开始是潭王朱梓,洪武十八年(也就是1385年)就去了长沙。
结果没几年,到了建文元年(1399年),他就因为卷入了“削藩”风波被废了。
接着是谷王朱橞,永乐元年(1403年)就藩。
可这位也没消停几年,永乐十五年(1417年)就因为谋反被皇帝给废了。
然后是襄王朱瞻墡,宣德四年(1429年)被封为襄王,本来是要去襄阳的。
结果因为长沙府空出来了,而且这地方太重要,于是就直接顶上了。
最后是吉王朱见浚,成化十三年(1477年)就藩,一直到明朝灭亡,这吉王府都还在长沙。
您注意到没有,这四位藩王的封号,跟长沙这个地方的名字都没啥直接关系。
潭王是因为长沙古时候叫“潭州”;谷王是封地宣府有个“谷郡”;襄王本来是去襄阳的;吉王更是直接取了个“吉祥如意”的好听名字。
这说明啥?
说明到了后来,藩王的封号和他们实际就藩的封地,已经没啥必然联系了。
这就像咱们现在给孩子起名字,不一定非得跟出生地挂钩,好听、寓意好就行。
更夸张的是,这吉王府,直接就是沿用了谷王府以前的旧址,稍微修修补补就住进去了。
这不就是咱们现在说的“拎包入住”嘛!
再看山东的青州府,这也是个“多事之秋”的地方。
齐王朱榑,他的封号“齐”就是取自青州属于古时候的齐地。
可这位王爷的命运啊,那叫一个坎坷,先后两次被废:先是被建文帝削藩,后来又在永乐年间因为谋反被废了。
接着是汉王朱高煦,这位可更“牛”了!
他被封为汉王,可就是不肯去青州就藩,赖在京城不走,最后也被皇帝给废了。
直到衡王朱祐楎,弘治十三年(1500年)才老老实实地去了青州就藩。
他也是直接沿用了齐王府,只不过又扩建了一下。
你看,这青州府,先是来了个“折腾王”,又来了个“赖皮王”,最后才等到一个“安分王”。
这过程,简直比咱们现在看的电视剧还精彩!
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例子,比如明朝迁都北京之后,原来在南京附近的一些王府,也得到了“循环利用”。
陕西的平凉府,安王朱楹因为没有子嗣,被皇帝给废了,王府就空了。

结果,韩王朱冲(这个字念“huo”,火字旁加一个或字)就直接搬进了安王府。
还有湖广的安陆州,郢王朱栋和梁王朱瞻垍,这两位王爷也都是没有子嗣被废了。
结果,后来的兴王朱祐杬(就是后来嘉靖皇帝的亲生父亲),直接就搬进了这两位王爷用过的王府,这简直就是“三手房”了!
说到这儿,您可能要问了,这藩王的封号和封地,到底是个啥关系啊?
为啥有的王爷封号跟封地有关,有的却完全不搭边?
这背后啊,是明朝封号制度的一个大变化。
在明朝刚开始那会儿,也就是洪武年间,藩王的封号还比较朴实,基本上都是直接取自就藩地的古称。
比如燕王,就是因为他在燕地(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一带);楚王,就是在武昌;潭王,就是在长沙。
这就像咱们现在给地标建筑起名字,直接明了,一听就知道是哪儿。
可到了永乐年间以后,藩王的封号就开始“放飞自我”了,跟实际的封地渐渐没啥关系了,而是开始追求“祥瑞美名”,也就是好听、吉利的名字。
比如吉王(在长沙)、兴王(在安陆)、瑞王(在汉中),这些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就高大上多了?
“吉”、“兴”、“瑞”,都是好兆头,皇帝赐给你的,就是希望你吉祥如意、兴旺发达。
再到了万历年间,藩王的封号更是彻底“符号化”了,成了皇帝寄托美好愿望的一个代号。
福王(在洛阳)、惠王(在荆州)、桂王(在衡州),这些封号,您根本看不出跟实际的封地有啥联系了。
这就像咱们现在给孩子起名字,不一定非得跟出生地挂钩,好听、寓意好就行。
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,明朝礼部在给藩王拟定封号的时候,根本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协调机制。
结果呢?
郡王的封号重复的现象那是屡见不鲜!
比如,在明朝的蜀藩和荆藩里,竟然都有叫“富顺王”的!
这要是两个“富顺王”凑到一块儿,不把自己给搞懵了?
还有那种藩王改了就藩地,但是封号却不变的情况。
比如辽王,最初的封号是因为他在广宁就藩。
后来他迁到了荆州,结果还是叫“辽王”。
这不就跟一个人搬了家,身份证上的地址没改一样嘛,多尴尬!
所以啊,明朝这种“藩王封号是唯一的,但王府却可以反复使用”的现象,说到底,是明朝的统治者在巨大的财政压力和维护宗室制度之间,不得不做出的一种妥协。
从经济上讲,皇帝是真的想省钱啊!
与其花大价钱去新建一座王府,不如直接利用现成的,能省一点是一点。
毕竟,明朝末年的时候,光是给宗室发俸禄的钱,就占了国家财政收入的37%!
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,要知道,这是全国老百姓辛辛苦苦交上来的税啊,都拿去养王爷了。
如果再不省着点,大明江山都得被这些王爷们给吃穷了。
从政治上讲,皇帝们还得维护“亲亲之谊”的表面功夫,不能让自己的亲戚们觉得被“抛弃”了。
通过赐予“祥瑞美名”的封号,既能给足王爷们面子,又能弥补地理资源上的不足,让他们不至于觉得住“二手房”或者“三手房”有什么不妥。
您看,这多像咱们现在的一些企业,为了节省成本,把办公地点搬到郊区,但对外宣传还是挂着一线城市的“高大上”名头,是不是异曲同工之妙?
然而,这种“拆了东墙补西墙”的做法,也暴露出明朝宗室制度在财政和权力控制上的深层矛盾。
朱元璋皇帝当年分封藩王,是希望他们能像屏风一样,拱卫大明江山,抵御外敌。
可结果呢?
到了后来,这些藩王们非但没能起到“戍边基石”的作用,反而成了国家财政的巨大负担,成了大明江山的“财政赘疣”。
所以说,这明朝藩王“一地一藩”原则下的“循环利用”大戏,其实就是一场充满了无奈、妥协和各种矛盾的大戏。
它告诉咱们,任何一项制度,在面对现实的挑战时,都可能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。
而这些变化,往往也预示着一个王朝的兴盛和衰落。
一直牛配资-股票配资炒股交流-炒股开户要求-配资炒股开户平台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